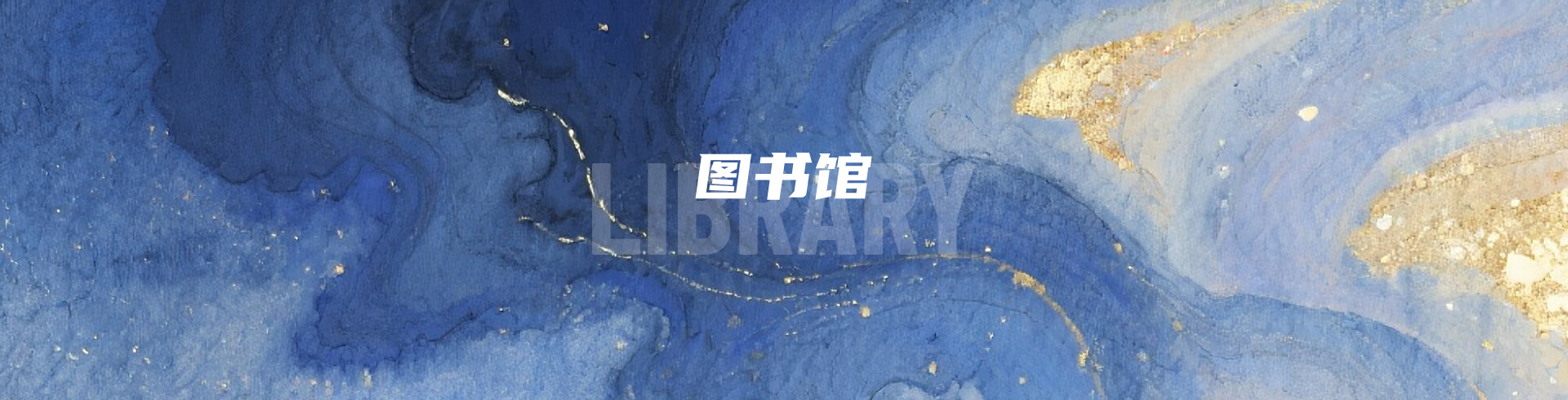
(九)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那位以“革命和理想”为标志的、勇敢坚毅、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的父亲,其实从来不曾与我的生命在现实中相遇,只是一位仅仅活在叙述和回忆里的人物,倒是那位背着沉重的宿命包袱的青中年父亲,才是我在现实世界里第一次遇见的父亲。还有那夹杂在主旋律里的不祥的音符,也开始不时粗暴地闯进入我童年和少年的春梦里。1962 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父亲离开了我,踏上了他生命中的另一段旅程。一直要等到 5 年以后的1967 年,我与父亲的生命轨迹才重新交叠。可是,天哪,在我的生命感知里,这离开父亲的五年,犹如古老的世纪一般的又漫长又丰富。我像一只安静敏感的小鸟,蜷缩在一个由我外婆外公,还有为数众多的大哥大姐(其实是我的舅舅阿姨)组成的,拥挤、艰难却温馨的大树浓密的树叶中。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透过来,既明亮又温暖,我感觉安全和满足。只有在夏夜里,当我亲爱的外婆为我哼唱家乡的童谣,我仰头数点天上的星星,这时候,远方的父亲才进入我的思绪,既遥远又靠近。父亲啊,你是我的精神的靠山,快乐的源泉,生活勇气的寄托。也许吧,正是借着这一份诗意的思念,我从小就具备了一种耽于玄思的抽象的气质。我对父爱的依赖,也越来越变得像哲学家说的那种纯精神的纽带了。那是我从5 岁到10 岁的一段金色岁月。
我的回忆的时间轮子,现在驶进了热闹的1966 年。那个不祥的黑色音符,如今已经成为了主旋律,如雷霆似地在头顶轰响。但当这场莫名其妙的风暴刚刚刮起来的时候,家里的年青男人(舅舅)们是莫名兴奋的。这份兴奋也感染了我,激起了我不安定的童年的好奇。那时候我在读小学 2 年级。我很快就会模仿报纸社论和街头大字报里大人们的批判逻辑和口气,开始写出小学生版的政论批判文章了。我批判的对象是小学语文课本里课文。我跟在舅舅屁股后面上街发传单。在我的十岁孩童的血管里激动着冲天的豪气,当印刷着革命檄文的五颜六色的传单,从我的软弱的小手里散发出去,纷纷扬扬,从天而降,我似乎已经成为父亲红色事业的接班人了。那像星星一般遥远的父亲一定会为我骄傲的。那时候,大人认真地告知我,我的家庭成分是革命干部。我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是父辈的(我父亲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可是,事情的进展并不像我希望的那么美好。我的安身立命的那颗由外公外婆组成的树叶浓密的大树,正在经历狂风暴雨的洗涤。外公因为历史原因,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此不公正迫害一直要到十年文革结束后的1979 年才得以纠正平反)。出于我对外公的爱,和对自己命运的恐惧,我开始在良知上无法认同这场革命。也正是在那段混乱的岁月里,我开始在朦朦胧胧中,培养了与世界拉开距离,用第三只眼睛审视世界的反省意识了。在潜意识里,我也开始用独立的眼光审视父亲的绝对正面的形象了。在学校里,我不再有兴趣写批判文章了。我很快发现了另一个更好玩的兴趣,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大批判漫画。我的才华再一次受到了大人的肯定。正是在那一年,父亲决定接我和二弟到父母工作和居住的山区龙泉,回到父母身边一起生活。那是1967 年,父亲 41 岁。我10 岁。(这里的文字,算是我对那场浩劫里我的红小兵身份的真诚忏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