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从上一篇奥古斯丁与帕拉纠(4-5世纪),到这一篇安瑟伦(11世纪),再到下一篇的阿奎纳(13世纪),时间跨度长达600-800年。似乎是上帝的命定,在奥古斯丁主义成为罗马教会正统以后,经过漫长岁月的酝酿,两位新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安瑟伦与阿奎纳虽然相隔2个世纪,却犹如心有灵犀一点通,联手开启了教会史上一个充满理性活力的新时代。对此,《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作者奥尔森是这样描述的:
“枯木逢春又发芽。基督教神学的创造力,经过长久苦旱的熬炼后,终于在11世纪苦尽甘来,因为西方教会对于神与救恩的理智思想,开始绽放出一株崭新的花朵。经院哲学派神学,崛起于欧洲所创立之崇尚改革的修道院,并在巴黎和牛津等新成立的大学里面盛行起来。在最初,大学只是聚集在大教堂与修道院之学校附近一群独立学者的群集。这些学者与学生打成一片的团体,就发展成为欧洲中世纪的大学。”
上述“经院”一词来自拉丁文的“学校”(schola),也是英文“学者”、“博学的”词汇的词根。经院学派神学新时代的使命是,在基督信仰光照下,探索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并把由奥古斯丁-帕拉纠之争引发的基督教内在张力,引向神学与人类普遍理性和方法的对接上。这场伟大的思想运动,从11世纪开始,到了13世纪达到了高峰。一头一尾,安瑟伦是伟大的先驱者,阿奎纳是登峰造极之杰出代表。
(二)
在进入正题前,我想与各位分享我对何为神学与神学家的7点默想,作为下文的铺垫。
(1)什么是神学?什么是神学家?对此,我能想到的最直接了当的回答是,“神学”是站在人的角度去理解和表达作为“绝对者”(也就是“神”概念的哲学表达)到底是怎样的存在?“神学家”就是努力理解和表达“绝对者”的人当中,那些持之以恒,卓有成就的佼佼者。就好像“数学”理解和表达数学,“化学”理解与表达化学一样,神学也是一门学科,这门学科理解和表达的对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因此“神学"也被称为“形而上学”。
(2)那么,“神学”与圣经的区别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说,圣经66篇书卷的作者都是神学家呢?我认为不可以。圣经作者不是神学家,他们之所以写出了圣经是因为他们受到神的直接启示。他们犹如先知,是神对人类说话的代言人和执笔者。这是圣经信息的核心和主要部分,而圣经作者出于自己的对神的理解与表达部分,虽然也很重要但是次要的,属于延伸和辅助性的。
(3)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平信徒与圣经的关系,和与“神学”的关系,是不是有区别?哦,区别太大了!可以用成语“天壤之别”来表达。圣经是神关于救恩的启示,因此直接关系到人的救恩;而“神学”只是人做学问的成果,是人的理解力和创造力的产品而已。借用保罗的话来说,神学家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用我的话说,神学家说的是“道理”;圣经强调的是“真相”。
(4) 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件事,所谓教会史,一般都是写对教会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和事件。他们大都是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和掌握权力的神职人员和教会领袖,而不是写成千上万在基督里生命得救赎的平信徒的故事。因此,教会史上的任何人,即便是最伟大的神学家,如奥古斯丁、阿奎纳、马丁路德等,都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以罪人的自觉意识直面赐救恩的神,这时候他只是一个平信徒,无论他是不是神学家或教会领袖都一样。他们与我们团契里任何一个成员一样,读的是同一本圣经,领受的是同一个圣灵。另一个身份是由各人的天赋才华和经历决定的各种社会职业的标签: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医生、律师、老师、厨师、司机、管家等等,也与我们团契里任何一个成员一样,因为我们也有我们各自的职业。
(5)这样看来,神学家关于神的思辨成果,在本质上看,对于我们来说,就如同其他各种“家”以及普通人的劳动成果一样。这些劳动成果,或作为精神性的知识,或作为物质性的消费产品,被我们享用。我们可以从中受益,我们也可以从中受害。无论是受益还是受害,它们都是人的产物,与圣经的启示是绝对不可比拟的。所以,我们读教会史和神学家的思辨产品,无论认可还是不认可,都不能与我们直接读圣经的经历相混淆。
(6)另外,还有一个区别需要注意。就是神学家以神学家的身份所作的神学思辨,和所构建的神学教义和体系,与这些神学家以罪人和平信徒身份,所作的读经默想和笔记,是不一样的。对于他们的罪人与平信徒身份,可以看作是我们团契里一个跨越时空的弟兄姐妹,借着他们留下来的文字,我们可以就具体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进行交流并寻求达成理解上的共识,就好像我们目前在团契交流里所作的一样。可惜的是,许多教会史上伟人的第一性读经默想和笔记,并没有引起教会里后人的重视,甚至也没有引起他们自己的重视,因此大部分都没有流传下来。教会史的聚焦点和流传下来的,往往是神学家在神学研究上的思想成果。
(7) 圣经是直接由神而来的关于救恩的启示。这些启示借着犹太人与神互动的真实历史,代代相传,一直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见证,达到了完全和高峰。所以说,圣经强调的是一致性和不变性。耶稣基督以后再也没有新的启示。但是,神学家的工作恰恰是从领受圣经启示后才开始起步,代表了人类对神的理解和表达,一代接一代,推陈出新,就像接力跑一样。每一个神学家的工作,都离不开前辈们的工作,和自身所处时代和自身经历的影响。
(三)
安瑟伦出生于1033年的意大利。他出生的那一年离耶稣十字架事件已经足足过去了一千年。意大利后来成为13-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与安瑟伦和阿奎纳(两位都是意大利人)的诞生是分不开的。安瑟伦自幼天智出众,可称为神学界的神童,犹如音乐界的莫扎特,诗歌界的海涅,数学界的高斯, 物理学界的伽利略和牛顿、百科全书式的天才达芬奇等。不过,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位神学界神童的出世,才有了后来连续几个世纪天才辈出的欧洲文明新时代。
安瑟伦深受虔诚的基督徒母亲的影响。他幼童时的成长环境是新兴的修道院学校。童年的安瑟伦就对圣经和宗教事物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兴趣和想象力。他23岁离开故乡,去了法国著名的贝克修道院求学。4年以后正式转成了修士。由于他天赋的思想、写作和行政管理的才华,30岁就担任修道院的副院长,45岁成为院长。这期间,安瑟伦陆续出版了两部影响深远的神学著作,《独语》和《证据》。在这两部著作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轰动了当时欧洲思想界,成了教会史上里程碑式事件。1093年,安瑟伦60岁,出任了当年天主教在英国最高神职。后来由于与英国世俗国王发生矛盾,两次被放逐。1109年在放逐中去世,终年78岁。
安瑟伦一生勤于思考,笔耕不辍,除了《独语》、《证据》以外,还写了《神为何化身为人?》、《圣灵感孕与原罪》、《论圣灵的由出》、《论预知、预定、恩典与自由意志之相和》等一系列神学名著。
(四)
据教会史家记载,1076年的某一天晚上,安瑟伦在法国贝克修道院作晚祷时,默想诗篇14篇里的一句话:“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在安瑟伦时代,并没有人公然自称为无神论者,因为任何人只要明目张胆否认神的存在,立刻就会有严厉的惩罚临到他身上。因此,安瑟伦很好奇,“愚顽人为何如此愚蠢”?他开始思考,一个人若不依靠神的启示,对神的存在,人是否能够发展出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论证?他对此问题的思辨成果,后来发表在《独语》和《证据》两本书里。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曾想到,正是这两本书,成了经院神学(哲学)新时代的开山鼻祖之作。安瑟伦也因此名扬世界。
考虑到一些读者对“本体论”一词不甚了解,我摘录了百度百科的条文解释。“本体论(Ontology),是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质的哲学理论。“本体论”一词是由17世纪的德国经院学者戈科列尼乌斯首先使用的。从广义说,它指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这种本性需要通过认识论而得到认识,因而研究一切实在最终本性为本体论,研究如何认识则为认识论,这是以本体论与认识论相对称。” ----- 因此,安瑟伦对“神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这句话的意思是,安瑟伦希望从我们对神本质的理性理解里,推理出神真实存在的合理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思考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上,安瑟伦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体,即用祷告文式与神对话,就好像犹太人向神献祭一样,把自己深深关切的人生问题摆在祷告里,通过在祷告里自问自答,思索各种可能答案,并祈求神透过理性把智慧分赐给人类。以下是他在《证据》一书里的一段话,生动地反映了他写作的风格。他写道:“哦,主啊,我并不是努力要了解你的崇高伟大,我不会愚笨自到自以为能够这样做,但我期待能够多少知道,我衷心相信并且喜爱的你的真理。因为,我不是为了寻求认识,来使我可以相信,但我相信,为了使我能够知道。因为,相信,除非我相信,我就不会知道。”
这段话里的“我相信,为了使我能知道”,后来成了那个时代脍炙人口的名句,被后人看作经院神学的划时代宣言。安瑟伦的意思是明确的,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上,信仰(即相信)在先,理性认知(即知道)在后;但信仰是为了更好地建立理性认知。安瑟伦代表了一个新时代向基督教会的传统提出了挑战:若人在基督教信仰里不能生产出对世界的新知识,这个信仰就是假的。
这样看来,后人误解安瑟伦是一个贬低信仰的理性主义者,是不符合事实的。恰恰相反,准确地说,安瑟伦是一个高举信仰的理性主义者。只不过,安瑟伦所表达的“信仰”(相信),决不是今天许多教会里盛行的拒绝理性的卡通信仰:即“因为我相信了,所以我已经(或不再需要)知道了”。安瑟伦认为,只有当圣经话语客观地照亮人的思维时,人才会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和人自己。因此,信仰与理性认知不仅不矛盾,而是前者“生出”后者的关系。换言之,关于“愚顽人为何成为愚顽人”的问题,安瑟伦的回答是,因为没有信仰,所以成了愚顽了。安瑟伦这个观点,与保罗《罗马书》立场,“人因为悖逆而无知,因为无知而悖逆”,完全一致。
且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或者,你为什么能够肯定)神是存在的?一般基督徒的回答是,因为圣经(或摩西)如此启示的。或者再加上一句:因为我相信圣经说的是真的,所以神一定是存在的。可以说,安瑟伦以前的教会都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当安瑟伦提出不从信仰出发,而用天然的理性来推理神的存在,单是这个想法本身,对于当时教会的传统来说,足以“一石激起千层浪”了。
(五)
以下是我从《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一书第21章里摘取的两段文字,来说明安瑟伦“本体论证明”的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记录在《独语》一书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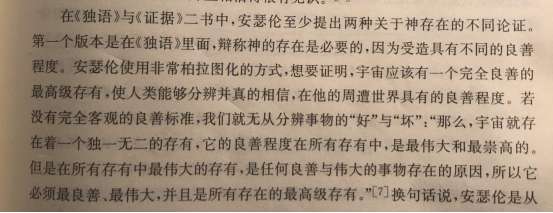
读到上面这段文字,我第一个联想就是,C·S·路易斯先生在《返璞归真》一书的开头,原来是根据安瑟伦第一版本的亮光写的。
“人人都听见过别人争吵,争吵有时候听起来很可笑,有时候只会令人不快。但是不管听起来如何,我相信,从他们所说的事情中大家都能够认识到很重要的一点。他们说:“别人若这样对你,你有何感受?”“这是我的座位,我先坐在这儿的。”“随他去吧,又不会妨碍你什么。”“你为什么插队?”“给我吃点你的橘子,我把我的都分给你了。”“得啦,你答应过我的。”人们每天都说诸如此类的话,不管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这些话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说话人不仅在说对方的行为碰巧令他不高兴,他还在诉诸他认为对方也知道的某种行为标准。对方很少回答说:“让你的标准见鬼去吧。”他差不多总要极力证明自己做的事实际上并不违反这个标准,即使违反了,也有特殊的理由。他假装眼下有特殊的理由使先坐这个座位的人不该再坐在这里,或声称对方在分给他橘子时情况与现在大不相同,或出现了变故,他可以不信守自己的诺言。实际上,双方看上去都像知道且都认同某种有关公道、正当的行为、道德等法则或规则似的,否则二人就可能像动物那样去打架,而不会在人类的意义上去争吵。争吵的意思是极力表明对方错了,假如双方对是非没有某种共识,只极力表明对方错了毫无意义,正如没有共同认可的足球比赛规则,说一个球员犯规毫无意义一样。这种是非律在过去被称为自然法。今天我们谈“自然规律”,指的通常是万有引力、遗传、化学规律等,但是以前的思想家称是非律为“自然法”时,他们指的实际上是人性法。他们的观点是:就像一切物体都受万有引力定律、有机体受生物规律的作用一样,人这种造物也有自己的规律。但是有一点重大的区别:物体不能决定自己是否服从万有引力定律,人却能决定自己服从还是违背人性法。”(摘自CS路易斯《返璞归真》)
简言之,人互相争吵不休的事实,恰好说明了,在每一个人(即便他是愚顽人)的内心深处都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可以被大家一致公认的绝对者(至善,至真,至义)存在。否则人之间的相互比较和争论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人理性里这个“明明可知”的“人性法”,其实就是安瑟伦“神存在之本体论证明”的第一版本。
(六)
后来,安瑟伦觉得第一版本还不够完美。他在《证据》一书里,提出了他的“神存在之本体论证明”的第二版本。以下摘自《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第21章另一段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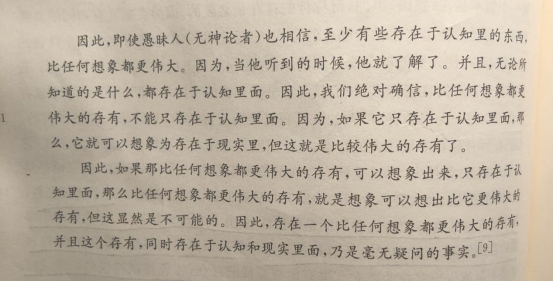
这段文字读起来有点拗口,我可以尝试把安瑟伦第二版本,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推理的格式,复述一遍。
大前提:所有人都知道,真实存在的事物,比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事物,要更伟大:
小前提:按照人对上帝的理性定义,上帝是所有事物中最伟大的;
推理及结论:若上帝只存在于想象里,它就不可能是最伟大的。因此,上帝只能是真实存在的。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借用圣经的启示,仅仅从人的先天理性出发,完美地证明了,神存在的真实性,是合乎人的理性认知的。也就是说,圣经关于神存在的启示,与根据人的天然理性推理得出的认知,是一致的。
安瑟伦的第二版本也印证了保罗在《罗马书》里一个重要论断:“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顺便提一下,保罗这里的“显明”一词,更接近圣经里特别强调的、人用经验到的客观事实所作的“见证”。而安瑟伦“神存在之本体论证明”这句话里的“证明”一词,是指圣经启示的“神存在”,是合乎人的天然理性的逻辑“推理”的。
回到安瑟伦对诗篇14篇句子的默想。愚顽人为什么如此愚顽?在第二版本里,安瑟伦表达了他的第二层看见:所有人(包括说“没有神”的愚顽人)心里都先天地拥有“三段论”理性;可是他居然还说“没有神”,正说明了他是真的愚顽透顶了。因此结论是:神定他(也就是所有的无神论者)为罪人是绝对公义的。
记得第一次读到如此简约完美的论证,令自称理性主义者的我,叹为观止。安瑟伦也因此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根据理性逻辑,不依靠神圣启示和信仰,来描述有神论信仰的神学家。后来的逻辑学家都会引用他的这项开创性贡献作为教本的案例。从此以后,特别是13世纪的阿奎纳以后,大批杰出的自然神论信仰者,他们中包括了许多富有创造力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也开始有了信仰与理性思维携手起步的第一块踏板。
(七)
在提出了“神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以后,安瑟伦一鼓作气,开始把对神的理性思辩,聚焦在一个更加开阔的问题上:这个一定存在的“存在”(神学家称为“上帝”;哲学家称为“绝对者”),必须具有哪些本性与属性?换言之,安瑟伦不想依赖圣经,或任何其它神圣启示的特殊来源,而单单依靠人天然的理性能力,去推导和思考上帝具有哪些本性和属性。
回顾教会史上记录的教父时代的信仰者,他们根据圣经启示神自称“自有永有者”,得出神这个“存在”的最重要本性是“不变性”,即祂的意志不依赖任何他者的意志,不依赖自身以外的“因”,也不随时间和历史而变化。由此推理,神不会因为人的祷告而改变。安瑟伦追问,若是这样的话,神就不是“最善良的”,因为“最善良的”必须具有听人祷告的怜悯之心。安瑟伦继续追问,如果神没有怜悯心,他就不可能是最善良的;但如果他有感情,他就会受到受造物的影响,这就不合乎神的“不变性”。到了这个地方,安瑟伦开始用祷告语写道:(以下摘自《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第21章一段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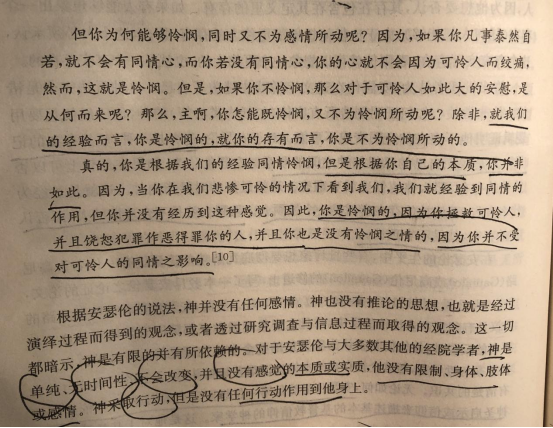
从上述文字里,我们看到了,安瑟伦对神的理解和看法,已经具备了18世纪伟大哲学家康德的“二律背反”性。当然也可以说,后世的康德受了安瑟伦之思想张力的启发。安瑟伦明确表达了,作为“绝对者”的立场看神,神是一位没有感情,也不需要透过调查研究而取得信息,因为这一切都暗示了,神是有限的并有所依赖的。因此,根据神的本性,神必须是单纯的、无时间的、不会改变的、没有限制的、没有身体和感情的;神采取行动,却不被任何他者的行动所影响。但若从人对神的体验的立场看,作为“位格神”的许多属性,比如神是怜悯的、听祷告的、具有强烈激情的、会后悔的、有慈爱的等等,似乎与神的本性是矛盾的,但这是因为它们是基于人对神的体验的立场说的。因此,人对神的经验,与神之本性之间,构成了二者同时为真的两个100%。这就是安瑟伦的“神论”,也是康德在700年以后用哲学语言“二律背反”所表达的理性的悖论。这样看来,比安瑟伦早600年的奥古斯丁与帕拉纠之争,正是“人之体验”与“神之本质”之间“二律背反”之悖论的绝佳例子。
(八)
安瑟伦在神学上的第三个重大贡献是,他提出了“救恩论”的“补赎说”。对此,我需要作特别的说明。关于耶稣基督对人类的救赎,新约圣经的使徒们强调了这件事(“救赎”)是真实的。整本圣经,包括了旧约与新约,都为“耶稣是弥赛亚”这个历史真相作了见证。对此,神学家作为平信徒,可以加入众多见证者的队伍,继续提供个人的生命见证;但作为一个有成就的神学家,他们的工作是不断提供符合人类理性并便于人理解的关于救赎的理论,来解释神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救赎罪人?对此,在安瑟伦时代,教会普遍接受的解释版本是由七世纪教宗格列高利提出的“救赎论”。《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第21章是这样归纳格列高利“救赎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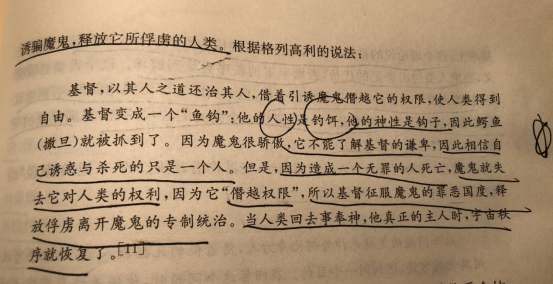
可以说,在整个中世纪时期,罗马天主教几乎全体一致传讲这个救赎理论,一直到了安瑟伦出现,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安瑟伦敏锐地指出,上述格列高利的救赎论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在救赎论上,把神与撒旦放在太接近的平等地位上。安瑟伦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挑战说,神是至高的存在,怎么可能在对人的救赎上,与撒旦讨价还价作交易呢?1098年,安瑟伦在《神为何化身为人?》一书中,以对话的方式集中讨论一个主题:神为什么,以及有什么必要性,化身为人,借着他的死亡,来拯救人类?在书中,安瑟伦把“补赎说”的纲要,作了如下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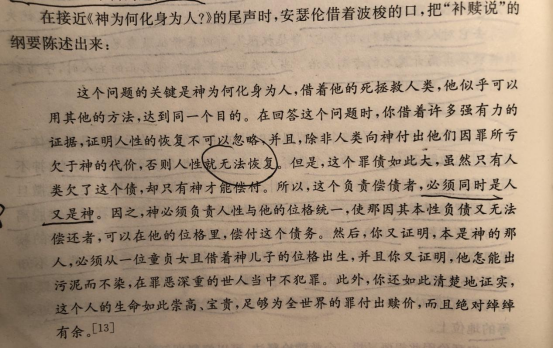
关于“补赎说”,安瑟伦曾多次说明,他用了“家臣破坏了封地领主的契约时,要付出满足领主之代价”的习俗和意象,作为神对人类救赎救的一个类比。根据这个类比,人类因为不顺服而欠神的债,神的公义要求人类下地狱的代价;但神出于怜悯,提供一个完美的替代牺牲,以满足他的荣耀,并且维护宇宙的道德秩序。这个最完美的替代牺牲,就是圣子耶稣基督。
显而易见,与格列高利“救赎论”相比,安瑟伦的“补赎说”,更加符合人类对至高者上帝的理性理解。因为格列高利“救赎论”的核心是神与撒旦之间的交易;而安瑟伦“补赎说”的核心是神与人之间透过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全新关系,借着挂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身体,神的公义和怜悯都得到了满足。(因此在成就人类救恩这件事上就不关撒旦什么事了)。
后人还发现,安瑟伦“补赎说”的最大亮光,是强调了神的救恩的客观性。圣子为了人类的救赎在十字架自愿受死,是一个出于神自己的客观行动和事实;而罪人因此真理的客观性,得以透过在基督里悔改、信心和礼仪,接受神的赦免和救赎。自从安瑟伦以后,安瑟伦的“补赎说”,几乎完全取代了格列高利的“救赎论”,成了教会里最有影响、最权威,也是最受欢迎的救恩论的解释理论。直到今日。
(九)
不过,正如我在前面说明的,任何神学家,无论他们多么杰出伟大,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工作都是出于人的理性思辨的产物,是基于人的立场对神的理解和表达而已。既然如此,没有一个神学家对神的理解与表达,可以成为绝对真理,可以不受到同时代人与后人的挑战、补充和创新的。对于神学天才安瑟伦来说,也是如此。他的“补赎说”受到了同时代人阿伯拉尔(1079-1142)的严肃挑战。至于200年以后横空出世的的阿奎纳(1225-1274),更是全面继承、挑战和发展了由先驱者安瑟伦开拓的几乎全部领域,包括他的“神存在本体论证明”领域。可以说,在“信仰”与“理性”双重滋润的肥沃田野里,到了阿奎纳时代,才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完)

《窗外的夕阳》摄于2020年3月5日,乐清至上海的高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