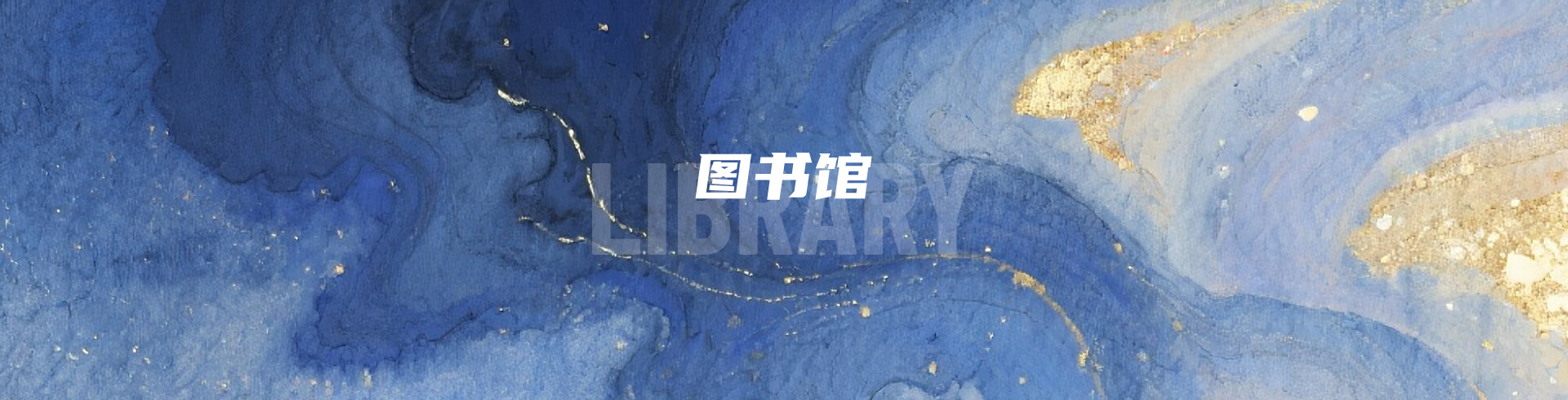
(1)让我先用一个切近生活的例子。比如说,关于祷告。神是不变的。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这是古今中外基督徒都会在信仰实践里遭遇的问题。当我们一边祷告,一边问自己,“神会因为我的祈求改变祂的心意吗?”这是一个真实的困惑。在这个困惑里,我们会不会向神打开心扉,继续问自己说,难道我需要神改变祂自己的心意吗?我真觉得神目前的心意还不够公义,不够良善,不够智慧吗?是什么让我有这样(“神还不够.....”)的想法呢?若你说,不,神啊,你不用改变。因为你是最公义,最良善,最智慧的。可是,且慢,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又是根据什么呢?我也许会说,根据圣经。可是,既然我这样想了(神不用改变),我又祷告什么呢?可是(又一个可是),我向神祷告错了吗?圣经不是也教导我们凡事祷告啊?
(2) 请问,上述关于祷告的自问自答,有没有也发生在你信仰生活里?另外,请注意,在这场对话里,我们使用的语言与我们平时与周围人谈话时所用的语言,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用的都是日常的语言。可是,我发现,至少在我的经验里,上述对话很快就会让我陷入了“自己打自己的脸”的困境。一方面,我祷告想要神改变心意,二方面,我因为知道祂是最公义最良善最智慧的(我怎么知道的?)而不要神改变心意。我陷入了自相矛盾。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当看见世界上不义和灾难时,我一边想,神啊,你看见了吗?另一边又想,神啊,你当然看见了,因为我知道,你是全智的。
(3) 我发现,在我们平时与人的交往里,会很少出现这样的困境(除非你把对方也看成神了)。虽然在我们平时与人的交往里也会有张力,但一般而言,要么是我打人的脸,要么是人打我的脸,很少会出现“自己打自己的脸”的奇怪局面。那么,为什么当我们的意念里出现神的概念的时候,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陷入“自己打自己”的困境呢?当这种困境出现后,我们的思维是怎样从进退失据的困境里逃离出来,回到正常的模式里呢?
(4)现在,让我们回到标题里的阿奎纳神学命题:人如何思考与言说神?阿奎纳说,人可以思考与言说神创造的“诸世界”,却不能思考与言说创造这世界的“神”。为什么?因为人不知道如何思考与言说神。为什么?因为创造诸世界的“神”与“诸世界”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人若用同样的语言和逻辑去揣摩神的时候,一定会导致对神的真实的扭曲与遮蔽。为什么?因为人所能作的任何思考与言说,都只能是基于自身对“诸世界”的有限经验,但神是无限的,神既存在于人对诸世界的经验之中,又存在于人对诸世界的经验之外。——在这段自问自答里,说者用清晰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人无法通过对诸世界的有限经验去思考与言说创造了诸世界的无限的神。 可是,对话中的听者也许在沉思了片刻后,平静地反问说,你说人无法思考与言说神,难道我们平时不是一直在思考与言说神吗?难道我们平时对于神的思考与言说都是错的吗?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不思考与言说神了吗?
(5)写到这里,我无法断言上述对话是否曾发生在阿奎纳那颗硕大的脑袋里。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借着思考阿奎纳,这段对话在我的脑袋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闪过,被我艰难地捕捉到并表达出来了。让我尝试着参与到上述对话的最后部分中去。1. 难道我们平时不是一直在“思考与言说”神吗?我的回答:是的。特别是我们基督徒。2. 难道我们平时对神的“思考与言说”都是错的吗?我的回答:不是的。这怎么可能呢?3. 难道我们因此可以不“思考与言说”神了吗?我的回答:当然不可以。特别是基督徒,怎么可能不“思考与言说”神呢?—— 在这个例子里,让我感觉奇怪的是,为什么在阿奎纳那里是天大神学难题(即“人如何思考与言说神?”),到了我这里,却根本就不是问题了呢?(请注意我的三个回答是:是的;不是的;当然不可以。)细究后我发现,我没有像对话中的说者那样,始终抓住我脑子里原本有的“先验观念”(“神是一位无限者”):更有甚者,在我的第一性反应里,连“神”的概念都经常是缺席的。难道说,我能够轻松地逃离了阿奎纳困境,是因为及时地放掉了我脑子里的“神”,以及与“神”有关的先验观念吗?
(6)上述细究把我带回到对安瑟伦的重新思考上来。安瑟伦从“上帝是最伟大的”这个先验观念出发,推论出“神存在之本体论证明”。为什么同样是“与神有关的先验观念”,在安瑟伦那里是强大的理性思维的源头活水,到了我这里反而成了自相矛盾的陷阱呢?我发现,当安瑟伦第一次向愚顽人发出挑战时,其实他也是向所有基督徒发出的。我问自己,在我时隔1000年后,听到了安瑟伦的推论后,为什么觉得他的推论不能令我信服呢?现在我看到原因了,因为我对有关神的先验观念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我认为那只是一些似真似假、似有似无的概念而已。如果安瑟伦问我,“你怎么知道上帝是最伟大的?”,我会回答说,“是圣经如此启示我的啊”。可见,我宁可承认圣经对我的启示,却倾向于忽略,所以也不愿意承认,先验理性对我的作用。所以,当安瑟伦说,一个人若在思维里没有了先验理性之光,这个人就离愚顽人的称号不远了。看来这话是真的。安瑟伦说的就是你与我。
(7) 好吧。我们不做愚顽人,不放掉先验理性之光。不逃离。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先验理性引起的困境吧。是的,上帝是不变的,是最公义、最良善、最智慧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如果上帝没有因为我们的祷告而改变,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如果上帝因为我们的祷告而改变了,那么,我们还相信先验理性(和圣经的特殊启示)是真理吗?在我看来,无论是不看祷告灵还是不灵(即依赖于先验理性),还是看祷告灵还是不灵(即依赖经验理性),都无法使我们干净利索地逃出自相矛盾的困境。是的,安瑟伦说了,信仰开启理性。可是,安瑟伦啊,这个被信仰开启的“理性”,确实让我看见了我所信仰的对象,本来就存在于我的先验理性观念里(安瑟伦出色地证明了这一点)。但除此之外,在我的经验世界里(这是阿奎纳所强调的),我该如何用正常的语言,去“思考和言说”我对它(信仰与理性)的体验呢?难道说,除了“自相矛盾,进退失据”以外,我就无法再用正常的语言去“思考和言说”了吗?
如此看来,我们在安瑟伦那里转了一圈,再一次回到了阿奎纳的神学命题:人如何思考与言说神?或者,人如何思考与言说,我们对神的认识与体验?
